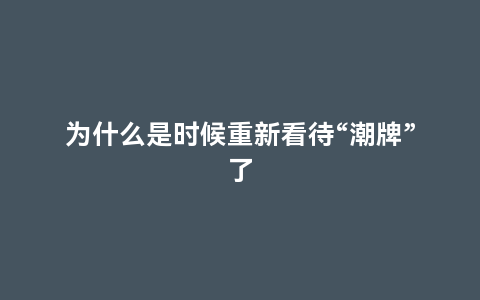
身为要报导他人作品的记者,总是认为艺术家们丢出越多讯息越好。但去年十一月当PyerMoss设计师KerbyJean-Raymond在推特上发表一则简单宣言时,开启了另一层面的对话。“感谢并欢迎刚开始报导PyerMoss的记者们,”这位海地裔美国设计师写道。“请避免将我们称为街头潮牌。这样太懒惰平面了,我们能给得更多,你们能做得更好。”在这两三句简短宣言中,Jean-Raymond重启了关于此用语及其单一想象的对话:有色人种(不管是设计师还是模特儿)的参与并非该风格是否为“街头潮牌”的决定因素。这种持续演变的类型源于滑板、冲浪以及嘻哈次文化,长期以来就如同字面上一样直白:代表着自立于主流时尚外,在真实世界中穿著舒适日常服饰的族群。曾为LadyGaga设计造型的NasirMazhar是第一位针对此议题抛出质疑的人,在2016年时指出时尚记者们使用此名词背后的偏见。这位由女帽转行为时装的设计师告诉记者TedStansfield:“大家一看到黑人或非白人模特儿穿上休闲轮廓,就认定其为街头潮牌。”时尚记者们不应采用这种近乎懒惰的刻板偏见。但在某些案例中,品牌对此卷标避之不及的态度也值得好好检视。除了不当使用外,“街头潮牌”常被形容为俗气、平凡,许多人更是看不上眼,但原因为何呢?设计师们也常将潮牌归纳到精品时尚的对立面,但一定要如此吗?Mazharelaborated继续解释他对此用语的不满,表示许多人对潮牌的态度为“这不是时尚,这要归纳在其他类别。时尚不是长这样的,时尚不是运动服,不是多元化,不是这些面貌。因此他们需要另一个名词的协助...Givenchy也有卖运动服、运动衫和T恤,但绝对不会允许自己被归类在街头潮牌!”像Mazhar一样的设计师当然可以自行定义作品的标签,但或许街头服饰的含义也在某程度上造就了此问题。时尚大牌们对此名词的偏见是事实,而其负面观感也是源于某种带偏见的精英主义。为何潮牌一定是个贬义词呢?历史上,这股次文化一直以来都代表着反时尚理念,但在渐成主流的过程中,拘泥于原始含义的态度也面临了矛盾困境,像是该如何归类2017年的LouisVuittonXSupreme联名系列。在此要思考的还有“文化挪用”在主流审美观尝试暸解街头服饰时所造成的阻碍。时尚顾问公司HavasLuxHub的AnaAndjelic在2017年Complex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表示:“文化挪用的现象非常常见,但多为扁平化的手法。就像是‘设计师撷取了这些灵感,混搭一下就推出自己的设计,但对街头没有任何尊重欣赏,不了解这是由音乐、街头艺术、在地多元又独特的族群交织而成的文化。’街头是非常时尚的。”我自己就见证过这种态度:在剑桥大学就读时,派对现场总是充斥着羽绒夹克、金色粗项链以及工作裤,每件单品都有外露拉链。这可能会令人感到意外,毕竟这里的人口组成与街头时尚的根源可说是天差地远;根据2017年的统计,81%的剑桥入学生来自社经地位排名全国前两名的群组。在主流品牌中,还是有成功处理潮牌这个标签的案例,并排除掉公然挪用与文化剥削等有问题的手法。当设计师及消费者对街头文化不在乎,或没有适度将收益分享给该风格的根源时,普及的街头服饰就是文化挪用的受害者。但有些设计师显然掌握的不错—例如Dior男装创意总监KimJones,他曾公开宣称街头风格是其设计灵感来源,但对此用语也是有所保留。街头服饰的政治寓意非常复杂—更不用提此类别在各方面都过于广泛模糊。虽然能有越来越多设计师对此用语展现善意是件好事,但只要街头服饰被挪用,或是被当作“非时尚”与“非白人”代名词的现状未改善,进步只会停滞不前。没人能瞬间改变“潮牌”的意涵,重新包装为所有设计师都想参一脚的概念。但看来产业界对它的态度应该大幅改变,更进一步尊重其文化源头。此风格含括并代表着时尚跨界刺激、动态又具颠覆性的力量。我们要保持警觉,别让这个词语承载了偏见,但也别忘了“潮牌”其实也不是个贬义词。MichaFrazer-Carroll为自由记者、gal-dem创办人与意见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