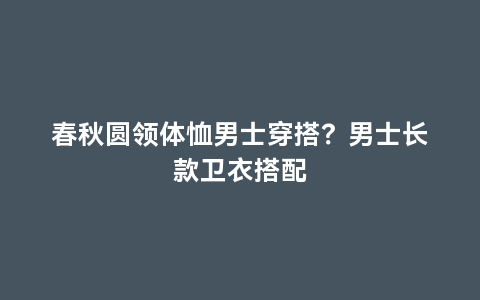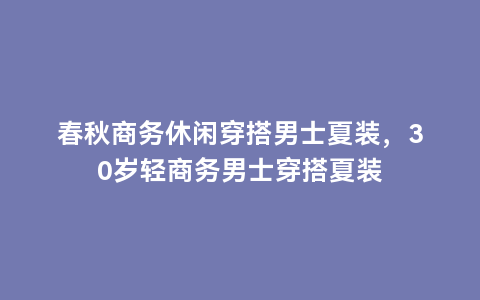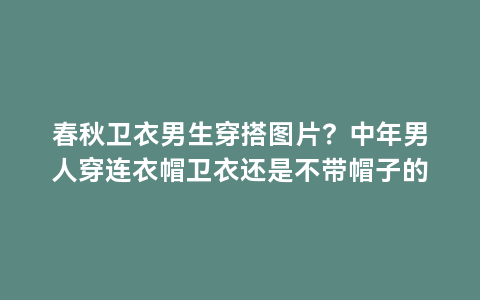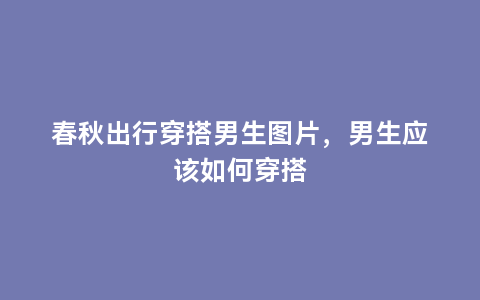“人并非生为女性,而是成为女性,”SimonedeBeauvoir在她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一书中写下了这句预言。这位存在主义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宣言——我们在不断演化,是无法定义的“多元态”——就像一柄利刃,无情刺向男性(masculinity)这个单元概念。随着它被解剖成无数碎片,暴露出其内在的各种微妙差别与复杂形态,单元男性就变成了多元男性(masculinities),从而可以有不同诠释,甚至变得脆弱起来,不再是过去不可一世的野蛮势力。Masculinities:LiberationThroughPhotography(多元男性:透过摄影获得解放)——一项新的国际展览以及随之而来的书籍——汇集了50多位艺术家的摄影作品,目的是探索多姿多态的男性特质,以及这个概念自1960年代以来的演变过程。Vouge特此邀请其中三位艺术家谈论男性对她们究竟意味着什么。CollierSchorr在她30年的职业生涯中,Schorr已经出版了十多本书,其中包括JensF(2005年)、8Women(20014年)和最近的Paul’sBook(2019年)——与法国模特PaulHameline的合作结晶。Schorr向来以她与Dior、SaintLaurent和Vogue等品牌合作的人像与时装摄影而闻名,她的作品关注身份政治和自我定义。你如何通过自己在Masculinities展览中那副名为Americans#1(2012年)的拼贴摄影作品探索男性概念?“[这副拼贴作品]由两部分构成:我[为TheNewYorkTimesMagazine拍摄]的一张年轻牛圈骑手照片,和从JacobHoldt一本[名为AmericanPictures]的纪实摄影书中摘下来的一页。我对纪实摄影家一贯所持的观察角度心存重重疑虑,更希望把观念投射于男性身份,而非阶级或受压迫的少数族群。我希望透过一位白人男性既呈现出他的被动性也呈现出他的侵略性。我希望展现男性并非一元概念而是一系列的神话。”‘女性视角’这个词被广泛用于指称女性摄影师。而男性摄影师就没有被类似地加以归类——你对这个词有什么意见?“如果你给我看20位女性摄影师的作品,我可能与其中一些抱持相同视角,但并非全部。女性摄影师有一百万种议程,而且来自一百万个不同的地方。我有时候疑惑是否男同志视角与直男视角之间存在差异,因为1980年代那些直女拍摄的女权主义作品与女同志拍摄的女权主义作品当然不同。异性恋女性与男性的生活关系更为紧密——而作为一名女同志,我不认为男性对我的工作有同样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我不认为摄影存在什么政治议程。它更多是私人化的——每个人都对彼此有某种感觉。”Paul’sBook(2019年由MACK出版)挑战了传统的男性概念。在其中,一张Hameline斜倚着的照片与一位拳击手DmitriySalita准备挥拳击打的照片形成鲜明对照。你会如何定义2020年的男性?“我以前认为自己知道对于男性是什么感觉,但现在我不是那么确定了,也许我根本不知道。Dmitriy是一个乌克兰拳击手,他为了逃离迫害跟家人离开俄罗斯来到布鲁克林。他是一个犹太人,拒绝在安息日比赛,于是力量与脆弱之间呈现天壤之别。我一直被一种想法所吸引,那就是男性表现出它无能为力的一面。“我不认为时尚界通过聚焦变性人之类边缘化群体的视角帮助改变了传统的男性观念,尤其是对大城市和创意圈子而言。不是说男性这个概念已经老派过时,更多是说它根本首先就是一种无稽之谈。”LizJohnsonArtur这位俄罗斯-加纳裔艺术家在2019年分别在南伦敦艺廊和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举办了两次个展。自从1991年搬到伦敦以来,她一直致力于记录非裔人(AfricanDiaspora)社群在此地的生活,不断为她名为BlackBalloonArchive的项目增添素材。你为此次Masculinities展览特别创作了WhenYou’reCool…theSunAlwaysShines——其中包含变装舞会众生相、早期大师画作的半针绣版本,以及EmmanuelBalogun的一首诗。这个作品背后的思路历程是什么样的?“我希望从一个女性的视角去探讨男性这个主题。我妈妈根据[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以及费尔巴哈的《伊菲革涅亚》]创作了半针绣手工作品;她从我十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创作《最后的晚餐》,用了两年时间才完成,所以说我是跟这副刺绣一起成长的。她做了很多半针绣作品。它们都是在家做的,她从来不卖给外人。就像我记录的那些Vogue舞蹈课——那些女孩纯粹是为了自己而去,并非想要取悦他人。”纺织品往往因为被视为一种女红而非艺术而遭人无视——通过在你的作品中加入半针绣,你是否是在对这种歧见发表自己的宣言?“摄影是我的工作基础,我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摄影师——我用模拟胶片拍摄,不使用相框——但在这里我想保护我妈妈的刺绣。我给它们加了个相框,为的是让它们有个安全的存在空间。我认为我们应该记住,缝纫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女性的一门技能,但男性也做缝纫。“[WhenYou’reCool…theSunAlwaysShines]是对我在拍摄时遇到的安全空间——俱乐部和舞蹈室——的一种投影。我遇到的一位舞者说他们开始练习Vogue舞蹈是为了抛弃那些男性化的动作。这对我来说很有趣——每一个细节动作都有详细规定,从你的手部动作,到你的脚部定位,都有要求。我在此想表达的观点就是男性可以是精致婉约的。”如今‘男性’对你意味着什么,这个观念是否曾随时间改变?“它不是我常用的词,但我想每次我们说起男性,我们就需要说起女性。必须有所平衡。CatherineOpieOpie被认为是美国当世最伟大的纪实摄影家之一,无论是从社会政治角度还是从字面意义而言皆是如此,她记录从酷儿亚文化到城市发展的一切主题,从中反映她对性别、身份和社区的关注。2009年她的密歇根湖摄影作品引起了巴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的关注。他把该作品挂在白宫墙上,并且在他总统任职期间一直挂在那儿。此次Masculinities展览有你的两组作品——BeingandHaving(1991年)和HighSchoolFootball(2007-09年)——你在其中如何探讨男性概念?“我一直以来都被人误认为‘先生’。在BeingandHaving中,我是在追忆我的那些朋友们以及我们当年如何表现男性阳刚气概——那时候,我们很多人在洛杉矶一个非常棒的俱乐部ClubFuck里面做变装秀。在每一幅人像中,我想要把[拍摄对象]从他们的环境中分离出来;我在一个黄色背景上拍摄他们,然后对照片进行剪裁,这样你就会把目光聚焦在他们贴的假胡子上。在我举办的一个展览上,有人误以为这些人是男的。我说,‘你认出这些其实都是贴着假胡子的女同志了吗?’人们一看到脸上有须发就理所当然认为那是个男人,我觉得这种反应很有意思。“HighSchoolFootball这组作品是想表现一类往往被塑造成刻板形象的年轻人脆弱的一面。到2008年,我们已经打了七年战,这些高中生可能已经奔赴战场成为士兵——于我而言,他们是美国境况的一种延伸。就像我在1990年代早期拍摄的一些好友后来死于艾滋病,我在这些男性身上也看到了脆弱一面。”自从创作这么多作品以来,你对男性的观念是否发生变化?“是的,在有了儿子之后,我想我的观念变了。我们生活在一个酷儿气氛很浓的社区,我曾经以为我已经够男人了,可以抚养一个男孩——我以为我会坐在那里跟他一起玩玩具车,跟他一起搭乐高,总之我小时候喜欢做的所有事情——但是我的这个男孩喜欢粉色,享受他这种身份流动性;他在5岁的时候,就写信给ToysRUs质问为什么要分男孩和女孩玩具区。我对儿子的身份有一种错觉,我需要质问我自己这种刻板成见。”为什么你认为务必对男性这个词持一种更加多元化的观念?“关于男性概念,各种各样毒害人心的说法是在太多了。举办一场展览,通过它质疑这种语言以及图像如何创造视觉历史——不仅关于性别,而且关于种族和文化多样性——那么就有希望在我们离开这个展览的时候,能认识到这其实并非那么简单。”你认为视觉文化在改变传统叙事上有多大作用?“我相信我能让别人看过我的作品就变得不再恐同吗?不,但我始终相信视觉文化非常重要。当人们跟我说他们在我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而且他们[随即]知道他们会好起来,这就是我能给予别人的美好。”
三位女性摄影师谈论2020年应如何诠释男性概念
本文来自网络,不代表服装搭配_服装搭配的技巧_衣服的穿配法_服装搭配网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fzdapei.com/136685.html